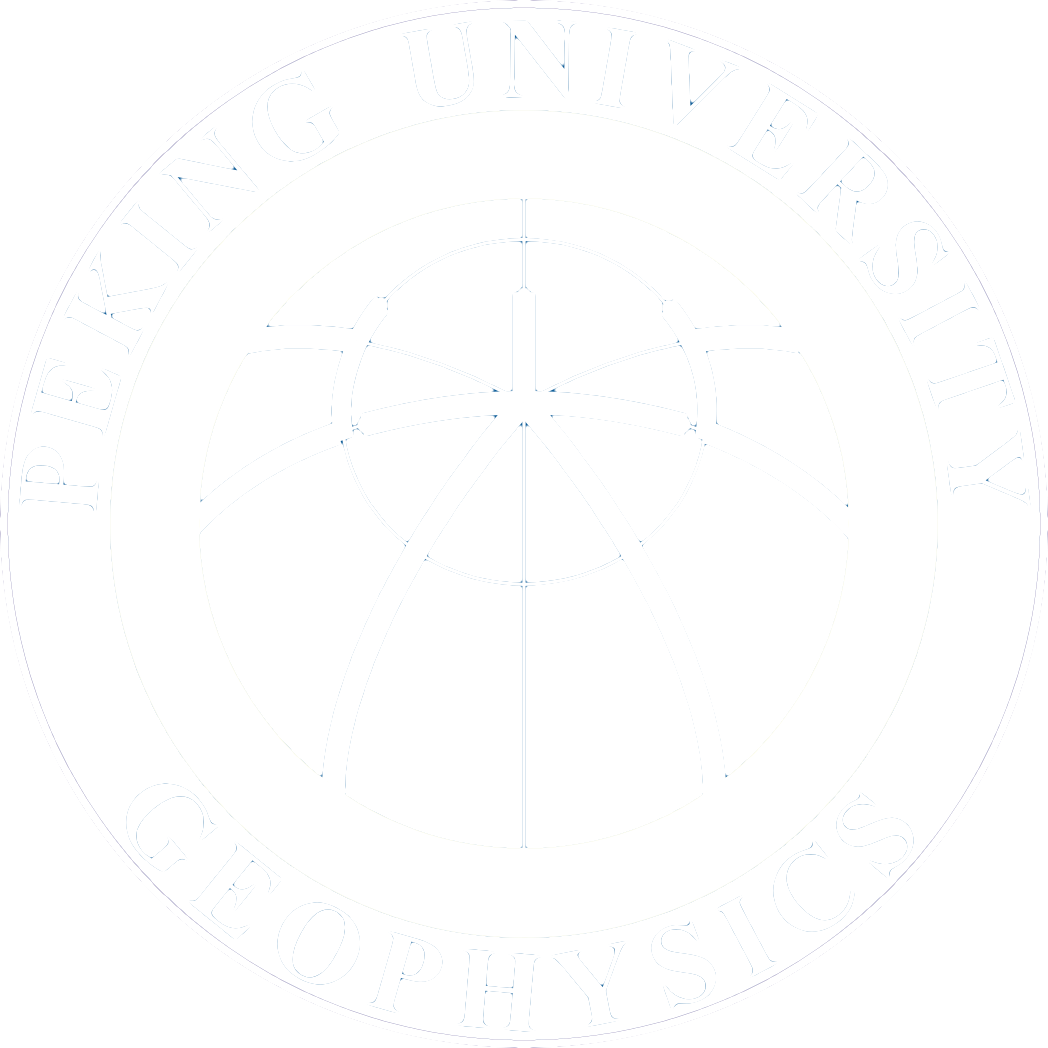2021-10-14
王克林
加拿大地调局太平洋地学中心、及维多利亚大学
Pacific Geoscience Centre, Geological Survey of Canada, and University of Victoria
我于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地震地质专业,是文革后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二批大学生。当时北大地质系刚从原来的地质地理系分出来,有四个专业:岩矿及地球化学(简称地化)、古生物及地层学(简称古生物)、构造地质及地质力学(简称地力)、地震地质学(简称地震)。77级只招了前两个专业,78级只招了后两个专业。所以,在那个春回大地、百废待兴的年代里,77、78两级合起来构成了北大地质系的首批学子,青春年少,踌躇满志,自命肩负着振兴祖国地球科学的使命,感觉任重而道远。但实际上,除了知道沧海可以变成桑田的道理和感受过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恐怖,我对地学一无所知。我那年高考成绩好到能进北大但又够不上物理、化学、力学等高分院系。北大的招生老师见我置之无用,弃之可惜,就顺手把我放到了地质系。老师公事公办、无心插柳,便初次锁定了我的科学生涯。一旦迈进地球科学的大门,发现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奇妙无穷,以至流连忘返。当时的老师们感受时代变迁比学生强烈,所以青春焕发,教学热忱极高。令我热心于地球科学的,首先是地质系许多老师的影响,包括蔡永恩、金凤英、孙荀英、孙荣圭、孙桂玉、邵济安、欧阳青、梁海华等等。当然,王仁老师的影响最为重要。
许多同门师兄弟、师姐妹在国内跟随王老师读过几年研究生,对他有更直接和深层的了解。相比之下,我和他近距离相处少一些,但这并没有妨碍我受益于他的指教。因为王老师在北大开拓了地球动力学,地力和地震两专业采用了在国内绝无仅有的课程设计。传统地质学的课程如岩石学、矿物学、构造地质、古生物等一门不缺,外加数次野外考察和实习。除了传授传统地质学,还高度强调数学力学训练。数学分析是和物理、地球物理等系一块儿上的(称物理类数学)。线性代数用的居然是北大数学专业的教科书,给我们讲课的数学系的老师还真按教材讲。结果是我们不光熟悉了矩阵运算,而且领悟了线性空间的内涵,为以后理解其他数学概念奠定了基础。后来地震专业因为特殊需要,又加了一些地球物理课程,如地震学,是地球物理系的傅淑芳老师讲的。后来我出国后发现,这种地质教学即使在国际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无怪乎78地震不少同学后来在地震局系统工作如鱼得水,包括赵和平、邱泽华、谢富仁、金星、孙亚强、陈建民、杨家亮等。
78地力、78地震进水楼台先得月,固体力学基础由王仁老师亲自授课,最后一小段改由殷有泉老师和孙荀英老师讲。不记得是殷老师还是孙老师,曾对我们说:你们以后就是“桥梁”,连结定性的地质学和定量的力学。王仁老师讲课不紧不慢,时常会像自言自语一样叨唠几句题外的话,大体都是关于某些概念更深层的含义、科研方法的一些哲理、或批评一些错误概念,都是些欲罢不能的肺腑之言。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听王老师的课,很喜欢这些即兴议论。别的老师一般没有这些议论。我记忆中,孙荣圭老师给我们讲普通地质时也曾有这类议论,令我受益匪浅。从我后来的研究经历看,固体力学基础是我在北大上的最重要的一门课,而应力应变这些基础知识由王仁亲自启蒙,真是我们78级学子的福气。这门课传授的知识和思维方法是全世界地学教育(不论是地质还是地球物理)明显缺项。我后来自己带研究生感觉最头痛的就是需要给他们补基础静力学。有些桃李满天下的地球物理学家能把波动方程舞得天女散花一般,科学难题攻无不克,却在力平衡、力矩平衡等小问题上败阵。例如有一个常见的说法,说年轻的俯冲板片热、轻、浮力大,顶着上覆板片,增加了他们之间俯冲断层上的正应力,造成大地震云云。这个说法就忘记了上覆板片的垂向力平衡。其实,断层上有多大正应力主要跟上覆板片多重有关,跟俯冲板片多轻没有关系。这类严肃的笑话并不罕见。
固体力学基础为我们打下的基本功,使我们以后研究地学时思维比较简捷。这在地学界静力学先天不足的背景下显得很突出。这一点我想78地力的尹安(后来在美国加州执教)也深有同感。我们在固体力学课上学到的一些常识,本以为谁都应该知道,但是随意说出来常令国际地学界同仁耳目一新,甚至振聋发聩。例如,我90年代开始研究俯冲带时,在卡斯卡迪(Cascadia)俯冲带有一个悬案。研究地壳应力的团队发现弧前地区主压应力近南北向,而研究地壳形变的团队发现主压应变近东西向。谁是谁非,争论了好多年。我走近一看,这有什么好争的呢?搞应力的测到的是绝对应力,而搞应变的看到的只是岩石形状在几年内的变化。如果形变是弹性的,这种变化只反映了应力这几年的增值,跟绝对应力毫无关系,完全没有必要在同一个方向。双方都是对的,只是分别看到了同一个系统中两个不同的重要现象。应力增值和绝对应力的区别本来是常识性知识,这一下成了大事,拨正了俯冲带地震研究的方向。当时,随便我到哪里讲这个原理,听众都有幡然猛醒的感觉。今天,地学界已经很少有人再在这个问题上有迷惑了。
我们固体力学课用的教材是王仁、丁中一、殷有泉著的《固体力学基础(地质专业用)》,1979年由地质出版社出版。此书集初等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弹性力学、岩石力学、流变学和有限元基本概念等为一体,强调地学应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还认为这本书是一流的好教材,还没有发现其中任何内容错误或打印错误。目睹国际地学教育在静力学方面的营养不良,多年来我一直有种冲动想把这本书翻成英文并补充更新,但一直没有时间精力实施。后来不知何故,此书在国内停止印刷,令人遗憾。现今还有一些绝版流传在世。其中一本在我办公室的书架上,纸质陈旧发黄,尽显岁月沧桑。我至今时时翻阅,核实基本公式,查找概念定义。想必三位作者在天之灵会为此感到欣慰。我的多数研究生都跟我借过这本书,包括不懂中文的学生(看公式)。十多年前,胡岩同学把它一页页扫描成电子版,给它以新的生命。
1982年大学毕业前报考研究生。我很想出国读研。当时改革开放起步不久,国门虚掩。说起外国,还是“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除非有海外近亲,欲想出国只能报考凤毛麟角的公派名额。只有少数教授手里有这些名额,也不是每年都有。在我们之前一年,王仁老师手里有五个这种公派名额。沈正康等北大地球物理系77级的考生如猛虎下山,一下卷走四个(另一个被兰州大学吴明东拿到),令我们嫉羡不已。但是,等到我们78级考研时,王老师手里一个名额都没有。沮丧之际,我开始计划报考地理系搞活动构造的一个出国名额。蔡永恩老师当时是78地震的班主任,一听就急了:“你怎么能不报王仁呢”? 然后就论述我为什么更适合学习地球动力学,说专业比出国重要。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但我还有一个顾虑。我说,王老师今年宣布从力学系和地质系同时招生(好像考试内容略有不同),恐怕更愿意招数学力学基础更好的力学系考生,未必真愿意招地质系的,我怕考也白考。他说“我去问问”。当晚他真闯到王老师家里去问了个究竟。第二天跟我说,王老师绝无偏向力学系之意,保证力学、地质考生一视同仁,按考试成绩录取。于是我决定放弃出国打算,一心报考王老师的研究生。就此,蔡永恩“夜闯王宅”,再次锁定了我的科学生涯。那年考取王老师研究生的还有78地力的赵永红和北大力学系的吴海青。但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没成想,我考上研究生两三个礼拜后,一个去加拿大的公派名额便阴差阳错地飞到了我的头上。不经意间,我还是变成了出国生。先在北大跟王老师读,83年底出国。再后来,改革开放更加迅猛,国门大开,中国留学生才像潮水一样涌向了世界。多年后,等自己弄懂了地球动力学的奥秘,我才理解王仁老师当年的良苦用心,明白我自己当时的顾虑完全是多余的。地球动力学是地学而不是力学。他想培养懂点地学的力学家,更想培养懂点力学的地学家。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桥梁”之说。除了固体力学基础和数学能力,他看重的是我们熟知岩矿、构造,有野外经验。这一点下文还会涉及。
1982年考上研究生后,开始跟王仁老师有些直接交流。跟他上过几堂连续介质力学,听他用英文授课。后来我被安排去西安参加出国生英文培训,课就中断了。也跟他上过讨论班,研究生们在他指导下读文章、讨论。这在今天很寻常,但当时很新鲜,极少有老师知道这么训练学生。当时蔡永恩老师是王老师的在职研究生(即一边教书一边读研),有一段时间曾带着我编有限元程序,在中科院计算所用当时的大型计算机(16K内存)穿卡算题。记得考上研究生不久,有一次同王老师一起从北大校园去中关村的北大技物楼。每人骑一辆自行车,边走边聊。我在北大本科四年,只知道上课、考试,完全不知科研为何物。我跟他说我感觉自己独立研究能力比较差。他仔细想了想,不解地问:“你为什么说你独立研究能力差呢”? 我也答不上来,但是他的语气清楚地表示,他和其他老师没有这种顾虑。我于是松了一口气。这也算是王老师无意中给我的鼓励吧。后来有一天我向他咨询应该申请加拿大哪几所学校。他说,你去西安大略大学学习大地热流吧,这是个很有希望的方向。这就变成了我的首选。于是,经王仁老师指引,我的研究工作就从在加拿大东部的西安大略大学研究地球的温度场开始了。先在实验室测岩石热导率,又在野外测井温,后来搞理论模拟。90年我迁到西海岸的温哥华岛,位于卡斯卡迪俯冲带的弧前地区(就是前面说到的主压应力近南北,主压应变近东西的地方),受大地震和海啸的威胁,于是开始研究俯冲带一些力学问题。因为在北大受过王仁老师的真传,再次捡起力学原理并不费力。
然后,忙忙碌碌,光阴似箭,一转眼又是三十年。今年纪念王老师百年诞辰,各种记忆自然浮现在眼前,值得挥笔(即敲键盘)。纪念科学界老先生,有一种常用套话,叫做 “德高望重,治学严谨”。恕晚生不用。“德高”用于雷锋比较合适,用来评价科学家有些不着边际;完全两码事。牛顿生前所作所为绝不能说德高,但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人类导师。“治学严谨”更是奇怪。严谨乃是从事科学研究最起码的要求。称赞大科学家“治学严谨”,类似夸奖名厨“饭不夹生”。我们从进入科学领域的第一天起便训练如何严谨,几十年不敢有一日懈怠,连搞科普都不可不严谨。不严谨怎么治学呢,岂不误人子弟?每一位杰出的学者都有自己的特点,每一个学生对他们都有独特的印象,都不是这些套话可以涵盖的。那王老师留给我的印象是什么呢?
王老师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尽职敬业。这不是“德高”,是专业素养。他本是塑性力学一方主帅,动乱年间落草地质系。天命之年学习新专业,拓展李四光地质力学。十年面壁,成为中国地球动力学开山鼻祖。他科学研究和教书育人都是楷模,这大家都知道。我清楚地记得他教导我们好好学习地质。初进北大的学生年少气盛,以为能写出复杂数学公式的学问才是科学,所以难免对地质课和野外实习缺乏兴趣。老师在野外左一个剪节理右一个张裂隙,兴致勃勃。而有些同学兴味索然。王仁老师给我们上课时则不止一次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要尊重这些教地质的老师,他们在野外很有经验,你们要向他们虚心学习。却原来,他自己就是这样跟这些老师学习地质的。这就是他如何面壁,开创新学科。当时我并不完全理解他这些话的意义,但是听得进去,也尽量去效仿。数年后从事独立研究,我才领悟到这些教导的深刻道理。地球科学是观测科学,需要大量的观测积累。身为地学专业研究人员,就要尽职敬业,脚踏实地,崇尚观测。只有懂得地质和地球物理过程,才看得见重大前沿科学问题。只知公式方程,编程运算,难免纸上谈兵。
因为有这种认知,我虽然以理论计算为主要方法,但是大量参与设计(偶然甚至领导)观测项目,包括地形变监测、海底测地、陆地和海底热流测量、大陆钻探、海洋钻探、海底地震监测等。我喜欢参观各种岩石力学实验室,了解实验手段和过程,每次都能回想起当年王仁老师带着我和沈正康等几个研究生参观地震局陈颙老师岩石实验室的场景。陈颙老师风华正茂,兴高采烈地给我们讲解,可惜我那时基本听不懂。我自己没有能力领导野外作业和科考航次,因而很羡慕林间、尹安、李正祥他们这些人有这种能力。但是如果能保证不成为人家的累赘,我尽量找机会跟搞观测的专家跑野外、出海。因为在北大受过地质训练,我在野外理解地质现象并不吃力。我曾多次随地质专家做古地震、活断层、老断层、岩石学的地质考察,也常常参与震后野外考察。我和中科院地质地球所的陈棋福老师(原来在地震局)一起多次考察海城和汶川地震震区。三年前还曾跟随地震局地质所的闻学泽老师在高原上考察鲜水河断裂。我天生没有方向感,在野外只能跟着别人走。但是因为熟悉各种各样的地学观测,在研究地球动力学时就知道方向,不用跟着别人走。
王老师留给我和其他所有人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基本科学概念非常清晰。这不是“严谨”,是专业功力。谁不想把问题理解清楚呢?但不是人人都能做到。我们尊王老师为“大师”,就是因为他能做到。1994年我回国参加他召集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会议场址是社会主义学院,在地震局地球所斜对面。顺便提一下,就在那个会上,我亲耳听到地震学大师安艺敬一(Keiiti Aki)尊称王仁为“中国地球动力学之父”(founding father of Chinese geodynamics)。我出国后主要研究热过程,当时力学概念有些生锈。会间茶歇时,在院子里聊起最近一些工作,我随口提到“应力释放”。王老师马上打断我,严肃而恳切地说:“应力是不能释放的”。 我马上意识到事关重大。这不是咬文嚼字,而是质疑基本概念。他研究力学炉火纯青,对每一个字都很敏感。有些似是而非说法,一般人觉得无关痛痒,到他那里就很刺耳。就像交响乐团的指挥,诺大个乐队里有一个乐器有一个音符不准,都难以容忍。这不正是我们作为科学家梦寐以求的境界吗?一个字用的不确切只是一个表象,它反映的往往是对一个概念体系没有吃透,没有建立物理直觉。一句话引起我一连串思考,举一反三,理清了一些基本概念。有说“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这算是“闻君一句话,胜读很多论文”吧。至今,不少地球动力学方面的论文仍然大谈“应力释放(stress release)”。这些文章对科学是有贡献的,但是可以断定,基本概念的不清晰限制了这些作者的研究深度和未来的研究方向。当然,有些不确切的说法是中外文之间翻译的问题。比如说王老师在给我们讲力学时还批评过“应力集中” 的说法,这只是批评它的中文含义,听着像把一个大区域的应力收集到一个小区域。起码英文“stress concentration”并没有这个意思,只是说在一个小区域里某个方向某个应力分量非常大。
我和王仁老师除了师生关系,是君子之交,没有什么私人来往。但是因为他女儿王鸣真与我夫人林臻是发小,我常常间接地知道他和他夫人的消息。二十年前,王老师在北京癌症病重。王鸣真从美国打电话来说她在加拿大找到一种特殊的给癌症病人的药,是一种液体,盛在大玻璃罐里,不知怎么能快速送到北京。正巧,78地震老同学赵和平率领着国家地震局的一个代表团正在温哥华岛访问我们研究所,马上就要返京。我问和平能不能带,他说这还用问? 王鸣真于是火速电话购药,安排快递服务赶在飞机起飞前交给了赵和平(那时手提行李可以带液体)。不幸的是,和平他们的飞机还没降落北京,王仁老师便与世长辞了。王仁老师给予过我很多的教导和帮助,我没能有任何回报。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倒是有这个机会参与帮个忙,无奈为时太晚,遗憾至今。